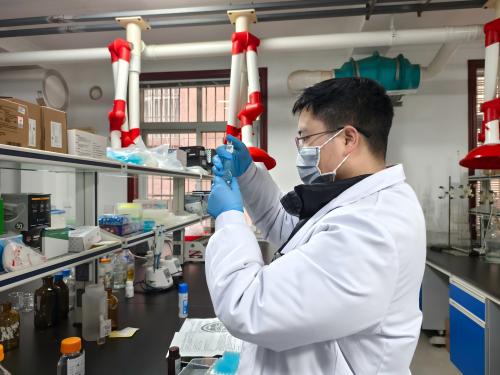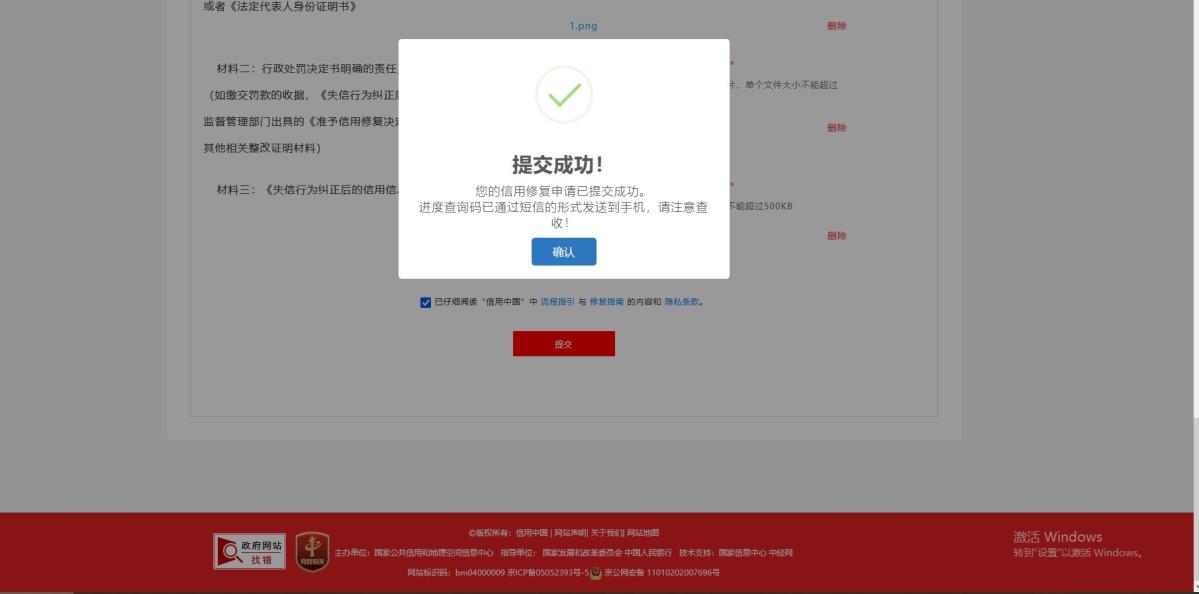202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10周年。
这一条千里长渠,从2003年开建算起,它历经10多年的建设,如今滋润着沿线26座城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亿。这一条千里长渠,一路北上,跨越山川平原,彰显着“中国精神”“中国智慧”。它让沿线人民从“有水吃”变成“吃好水”,也成为多个城市的重要水源。
2021年,邢台百泉泉域,断流30多年后实现稳定复涌,人们记忆深处的“水乡”重回眼前;今天,“华北明珠”白洋淀,碧波荡漾,鱼鸟翔集……湖北籍河北作家梅洁,十年前,一路行走、书写着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感人故事,完成了145万字的“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十年后,年近80岁的梅洁再次行走,她重返故乡,千里走“银汉”,为我们书写下沿岸的时代变迁、百姓生活和一个个为祖国、为家园奋斗不息、令人敬佩的平凡劳动者。
——编者

10月20日,南水北调中线滹沱河倒虹吸和退水闸工程。 河北日报记者田明摄
一
汉水从秦巴山大峡谷奔涌而来,三面环绕了生育我的湖北小城郧阳。
故乡,便如漂浮在水泊中的摇篮,我在这乳水的摇篮里慢慢长大。后来我少女时离别了故乡,离美丽的汉水越来越远。从秦巴深山到江汉平原,从江汉平原到北京,从北京到塞北大漠,从大漠转身华北平原,最终又梦一般定居在了首都北京。
同样,我也做梦都没想到,几十年沧桑之后,润泽了我幼年生命的汉水竟三千里迢迢北上,流进这座大都市,流进我的家,又流进我的生命中。
2014年12月,一个从1958年开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丹江口水库,开始向干渴的北方送水。甘甜的清水从河南陶岔渠首入渠上路,在郑州以西穿越黄河,沿京广铁路西侧、太行山以东,一路北上进京,输水总干渠全长1432公里(含从河北徐水分水至天津干渠155公里)。世界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丹江口水库调水北上,润泽苍生。
这是迄今世界上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引水工程;
这是宇航员在太空能够看到的一条三千里人工长河;
这是地球上的一条千里流淌的“银汉”啊!
夜幕下,站在汉江边,听着江水拍崖的浪声,我哭了……
1991年,离别故乡31年后的我回到了郧阳,我发现故乡沉没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了这汉江神圣的使命。
此后多年,我一直追随着她的使命行走:
我曾到达丹江口大坝由162米加高到176.6米的工程现场,我听到了开工庆典的鼓乐声;
我曾到达郑州以北30公里处探访“穿黄工程”,我下到了黄河竖井工程30米的深处;
我曾一次次返乡,送别一批又一批父老乡亲:湖北、河南两省几十万移民告别了世代家园;
我曾沿着汉水走了100天,折转身又在北方大地行走了100天。我虔敬地行走是在打捞一个庞大移民群体的告别与牺牲,也是在探寻一个被反复论证的工程实施的内在真因……
20年里,我伴随着汉水的使命长长短短地行走,汉水赋予我轻轻重重的责任与激情。
145万字的“中国南水北调中线移民三部曲”,是汉水源头那棵千年桂树上的三朵金色花,开在秦岭深处汉水初始上路的寂静山口……

梅洁在石家庄滹沱河畔。 梅洁供图
二
2024年12月,汉水进京第十个年头。
十年了,我多么想去看看汉水一路北上后的沿途风景。
十年了,我从没停止想象她的容颜、她的呼吸……
我终于能够出发了。
沿江水北上之路,我一路探寻。如同去探寻生命中的母亲,我快乐而虔敬地上路了。
我走上矗立于汉水的丹江口大坝。
我默默地回想,这是我第七次站在这座矗立于大水中的建筑物之上。
眼前,是浩渺无际的一库湛蓝。那水蓝得浸心,蓝得惊魂。阳光下,波光粼粼,水天一线。一座座露出水面的山头、断崖,被茂密的树林覆盖,形成一座座绿色小岛。这些小岛,如同水中冒出的一个个美丽精灵,静卧水中,接受着甘霖滋润。
在3000多米长的坝体中部,有一幅数米高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线路图,一位水利工程师在向人们讲述着中线工程十年调水的巨大效益。作为一直关注书写这项工程和移民的作家,内心的感动和惊喜难以自抑……
截至2024年9月,中线工程已为京津冀豫四省市输水670亿立方米,沿途26座城市、超1亿人口直接受益。
北京,如今南水占城区供水量的70%以上,1600万人直接饮用上了甘甜的汉江水;
曾经“吃的水能腌菜”的天津,如今,1300多万人用上南来的汉江水;
河南省,鹤壁、许昌、漯河、平顶山等许多沿线城市主城区全部用的是丹江口库区甘甜的水;
河北省90多个县(市、区)全部饮用上汉江水……
什么是幸福的最大指数?怎样感恩眼前这亿万人的生命之水?
站在176.6米高的坝顶,远眺浩渺水面,我想象着汉水在中国大地上的样子:
她从秦岭深处的嶓冢山流向长江的亿万年里,以其柔美的躯体写就了一个“人”字左边的一撇,这一撇长达三千里。当她在离嶓冢山九百余里处的丹江口水库分出一支流向北方、流向北京时,她又写成了这个“人”字右边的一捺,这一捺也是三千里。当我们的宇航员在太空遨游时,能拍下汉水在地球上写就的最美文字——“人”。
这便是几十万移民和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及建设者,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的一座无言的丰碑。这丰碑匍匐在大地,也耸立于云天!

北京团城湖800米汉水渠。梅洁供图
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程采用“自流”方式。
丹江口大坝最高蓄水位是170米,从陶岔渠首流出时水位是147.38米,终点北京团城湖水位是49.5米,长达三千里的输水线路,落差不足100米。这是一条多么不易的引水长路!
成千上万的工程技术人员、专家在数十年里,呕心沥血,昼夜奋战,攻克了难以计数的工程难题。三千里输水长路上,雄屹江水半个世纪的大坝、一座座宏伟的钢铁渡槽、江水咆哮的倒虹吸、地下几十米深的暗涵隧洞、滚滚流淌的千里明渠……无不是他们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是国内最大的水利枢纽改扩建工程,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大、工艺要求之高都前所未有。大坝是1958年由湖北、河南两省10万民工在汉水两岸的荒山野岭经历10年艰难困苦修建的。当年没有任何现代机械,全凭肩挑背驮、填土滚石,建成运行近40年。要在这样一个老坝体的背面和坝顶贴上厚达十几米的新的混凝土,把原162米高的坝体加高到176.6米,这新老混凝土结合的坝体能承载几百亿立方米的库水吗?
这是多年来民间的一个担忧和质疑。
这次寻访,无论是在丹江口大坝,还是在北京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在专家们讲述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时,我都凝神静听。10年蓄水送水,大坝经历了两次汛期蓄水170米极限高度,当320亿立方米极限水量浩浩荡荡压往库内,大坝巍然挺立,接受住了汛期蓄水的严峻考验。事实证明,加高工程确保了大坝的质量和安全,所有的技术攻关都创下世界之最。
听到专家的介绍,我在兴奋、释然的同时,也充满了敬意!
9月22日,我第二次来到了汉江、黄河相会的水利工程“穿黄工程”。
2012年,我下到了竖井的30米深处,看到德式盾构机在黄河底下雄猛地掘进……
“穿黄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穿越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项目之一,是中线总干渠穿越黄河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工程的任务是将中线北调的汉江水从黄河南岸输送到黄河北岸,向黄河以北地区供水,同时在水量丰沛时向黄河补水。
郑州西北约30公里的黄河孤柏嘴,两座建筑物巍峨矗立在黄河两岸。就在河床40米的深处,有深埋地下的两条隧洞将它们连通。“穿黄工程”的设计师们,用物理的倒虹吸原理,让从陶岔渠首上路奔流而来的汉水在这里一头扎入滚滚东流的黄河底部,从这条黄色“蛟龙”身下穿越而过,然后再从北岸奔腾而出。
多么震撼,多么壮观!
2005年9月“穿黄工程”动工建设,2013年底完工。这是南水北调的“咽喉”工程,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黄河古河道下开掘一项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没有任何经验和参考数据,河道下的泥沙、岩石,都会给掘进带来不可预计的难题。工程建设者们在数千个日日夜夜里,三班轮倒,每天挥汗如雨……
在黄河北岸的建筑物前,看到汉江水涛翻滚,从双筒隧洞里咆哮而出,滚滚向北而去;看到几十米宽的黄河之水在其上漾漾荡荡,东流不息……
内心的震撼与感动,被击成一河水声:这就是三千里北上的汉水啊!
迢迢北上。到达保定满城漕河渡槽时,太阳已擦身太行山苍茫群峰,光芒闪耀,从天峦一线的逶迤里,金箭般喷涌射出。泼墨般被染红的云霞,顿现万般瑰丽。
渡槽,是大型水利工程中的一个名词,就是用钢筋水泥搭建的引水桥梁。南水北调三千里输水北上,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渡槽跨越山谷和江河,将江水引入北方。
漕河渡槽是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境内,担负起从河北岗南、王快、黄壁庄等几座水库联合向北京应急供水的任务。
中线工程河北分公司工程师介绍,漕河工程建筑群由渡槽、节制闸、退水闸、检修闸、排冰闸组成。施工最大难点是底宽20米、长达2300米的跨越漕河的巨型渡槽。材料用量巨大、高空作业艰险、建筑物结构复杂,渡槽下每根水泥灌注桩的承载重量都是2000多吨,每根槽墩都深入河底数米,而每根槽墩的承受重量都是3万多吨……
中线长渠上,布建着无数的引水工程设施,引领着汉水“上天入地”,一路向北。
2005年8月,我从调水沿途采访归来,得知中线北京段西四环暗涵工程已于5月全面开工。这项工程施工难度世界罕见。那天,我在西四环桥旁边,看到一块用蓝色塑料布围拢的栅栏,蓝色围布上别着硕大标语“南水北调,精心施工”。
附近车轮滚滚、人流滔滔,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
我独自站在栅栏外呆想:在这个两千万人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地底下正在悄静而紧张进行的工程?有多少人知道南水北调真正的含义?有多少人会感动于不久就要喝上迢迢北上的汉江水?那天,我独自站了许久,许久……
漕河渡槽工程纪念碑,巍巍矗立在太行山的一座坡岭上。
登上山坡,站在纪念碑前,只见山下庞然的钢铁造物在夕阳下放射出蓝色之光。凝眸远眺,仿佛有一条金色的游龙正从瑰丽奇幻的云霞之海奔腾而来。
“南水北调,国之大策”,纪念碑上的赋文仿佛已浸润在沿渡槽千里而来的江水里,缓缓向北流去……

保定漕河退水闸。梅洁供图
四
我一定要再去看看石家庄滹沱河!
河北是我大学毕业后工作、生活了35年的地方。
滹沱河是石家庄人的母亲河!我曾经看到这条母亲河尘沙飞场。
我知道偌大的华北平原多么缺水……
可我还知道,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十年来,除为沿线输送优质生活水外,还为黄河等沿线50多条大小河流实施生态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汉水经过的地方焕然一新:千里长渠两岸,一片花红柳绿。
滹沱河呢?这条母亲河复苏了吗?
我把心思告诉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河北分公司调度师胥元霞。这位把一生贡献给了河北水利事业的女子,在退休离岗的当日,帮助我联系好一切。
初冬的阳光下,公司年轻的工程师王琎、谷鑫驱车30分钟,从石家庄市区带我来到正定的滹沱河倒虹吸工程现场。他们打开护水围栏门锁,当我跨进绿色铁质围栏大门,我一眼便看见清澈的汉水在工程渠内静静地流淌。一种惊喜和亲切掠过心头:家乡的汉水也流到这里来了呀!
沿着2900多米长的渠堤前行,王琎工程师边走边讲述:
2003年12月30日滹沱河倒虹吸工程正式开工,是南水北调中线干线首个开工项目。工程的混凝土浇筑、大型渠道衬砌等技术为后续调水工程施工提供了重要经验……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全长1432公里,其中河北境内工程长度为596公里。465公里的明渠在燕赵大地蜿蜒前行,29座倒虹吸工程穿河而过,渡槽、隧洞、水闸等与廊涿、保沧、石津、邢清4条大型输水干渠构建成河北“一纵四横”可靠安全的供水网络体系,已源源不断为全省多地输送南来之水。其中有几千万农村居民实现江水置换,使当地农村居民长期稳定地喝上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从2017年始,南水北调还为河北滹沱河、南拒马河、白洋淀等河流湖泊实施生态补水,使原来的河流湖泊迎来生态蝶变。目前,补水河道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生态基流,一批河流实现全线贯通,河道面貌焕然一新,干涸断流多年的泉眼复涌。如今的白洋淀,碧波荡漾,多种珍稀野生鸟类在白洋淀安家落户,野生鸟类增加至287种。
走出倒虹吸、退水闸工程,我们来到不远处的滹沱河畔,只见满河碧水微波荡漾,两岸花草葱郁、绿树成荫,河岸边有垂钓的人们,有跑步锻炼的青年……如今的滹沱河,四处皆是风景,已成为石家庄人运动、休闲、旅游的打卡地。
站在水清岸绿的滹沱河畔,我想到胥元霞调度师的一段话:
通水十年了,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过。中线调水工程关乎亿万人的生命,工程安全、水质安全、供水安全是天大的责任,所有人都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目睹滹沱河的巨变,我内心充满着感动:多么伟大的工程!这是一江清水带给世间的福祉!
9月24日,我第三次来到南水北调中线终点北京团城湖。
每一次南方、北方地行走归来,团城湖都是我伫立思索的地方。
为保证水质安全、免遭污染,北京段全程采用全封闭管涵输水。中线工程到达团城湖终点之前,设计了一段明渠,这是汉水进入北京后第一次露面。
至今,我都怀念时任北京市水利局局长焦志忠的一段话,他说:“南水北调是伟大的世纪工程,多少人为之奋斗和奉献。我们设计一段明渠,就是要让北京市民能够看见千里迢迢调到北京的水是什么样子,饮水思源,不忘生命之水的养育之恩。”
感激这一段充满人文情怀的工程设计,感激中国水务工作者和工程设计者赋予了钢筋水泥以温暖的人性。
南水北调中线对北京直接供水,通过与当地水联合调度,形成统一的地表水供水网络,供水范围扩大,覆盖北京平原区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断流了几十年的永定河,如今已实现河道全线通水,一片苇草森森、鱼翔浅底的水乡风景。
团城湖杨柳依依,烟荷娉婷。
北京人在这里打造了一处庄严的纪念南水到达终点的广场——甘露台。甘露台广场的南侧,九眼喷泉喷射着北京“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情怀,以及北京人民对南来之水的感激。
站在甘露台前留个影,为了这世世代代永不忘却的铭记。(梅洁)